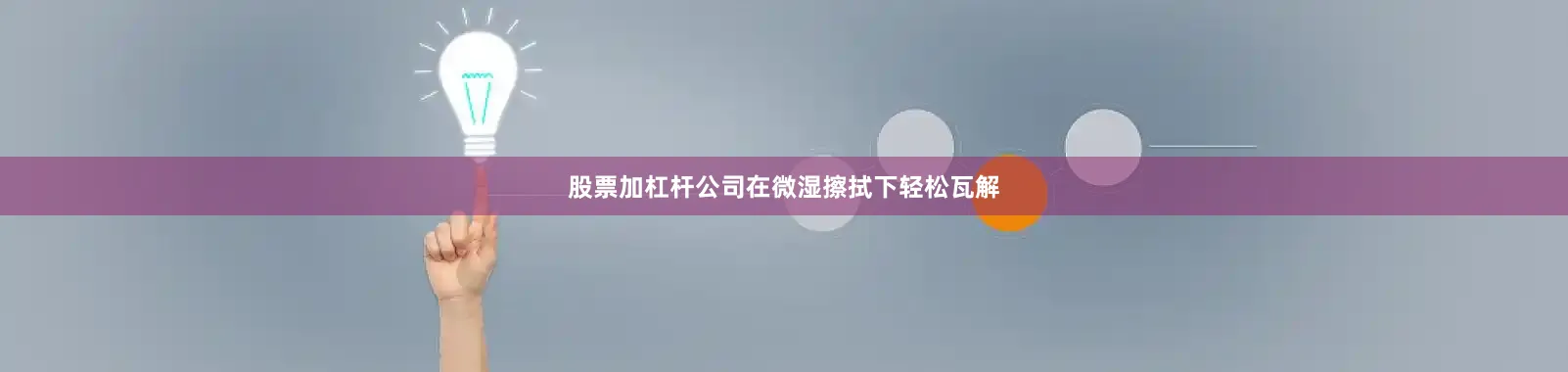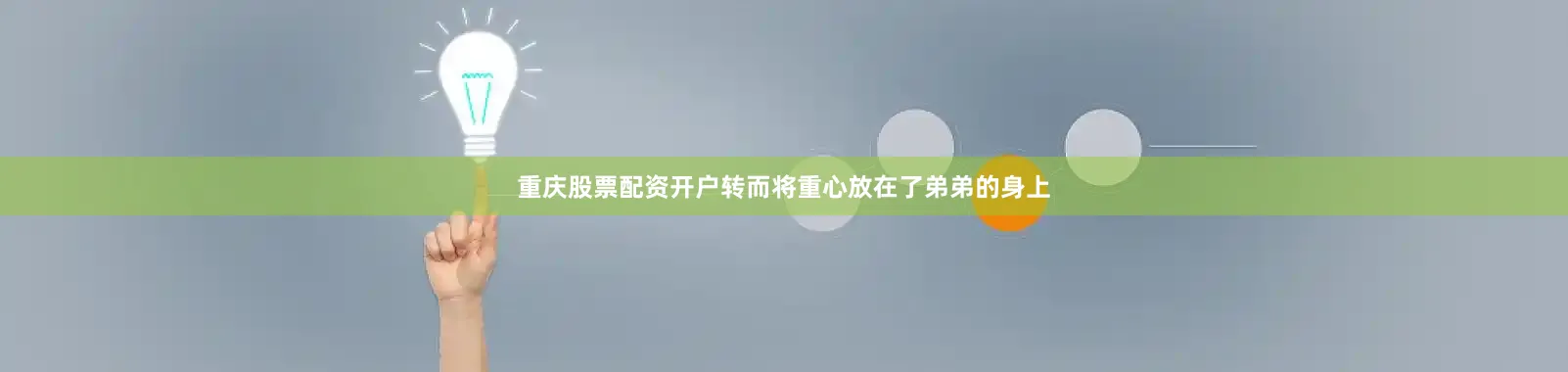
近几年,台剧发力有目共睹。
但评分天花板始终没变——
《我们与恶的距离》。


六年前的第一部,刷新了大众对台剧的认知。
而今年推出的续作,沿用原来的班底,也被赋以超高期待值。
谁知面世的过程却波折重重。
先是疫情影响。
再是剧中演员孟耿如,因牵扯丈夫黄子佼的台版「N 号房」事件丑闻被抵制。

《与恶 2》剧方只得应观众要求删减其戏份。
数次定档撤档后,终于播出。
口碑虽然不算差,但跟前作比还是掉了一档。

历来神作难逃续集魔咒,这部难道也一样?
来吧,看看咋回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 2》


续作翻车?
与第一部一样,《与恶 2》的故事也始于一桩无差别杀人案。
24 岁男子胡冠骏,在一家超市外纵火,点燃一辆摩托车。
火势蔓延,酿成 5 死 12 伤的悲剧。
犯罪者对罪行供认不讳,言行看似毫无悔意,引发众怒。

不过,两部的内容重点差异不小。
第一部聚焦犯罪过后,对众多社会议题进行自检与重建。
第二部的内容,算得上是对第一部的补充。
它尝试回答了前作悬置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无差别杀人犯?

要回答这个问题难度极大,绝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第二部评分下跌的原因,也由此而来。
比如,人物关系庞杂,时间线跨度大。
纵火案背后涉及 6 个家庭、几十个角色、前后 20 多年的纠葛。
内容细碎且每两集变换一次时间节点,带来混乱感,提升了理解难度。



十集的体量,很多人看到第四集才大概搞清楚人物关系。


更何况,剧集探讨的问题也远比第一部更具争议: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判他?」

这个问题,不仅司法界争论多年,现实中也几乎没有共识。
因为它触碰的是最根本的情感矛盾——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当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杀人,是否意味着他就可以不受惩罚?
那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又该由谁来偿还?

正是这种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其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挑战的姿态,投入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论之中。
也因如此,看完最后一集后,鱼叔反而确信这部剧没有烂尾。
我们仍能从貌似繁冗的故事里,看到依然锋利的「问题之刃」。
最核心的那把刀,正对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此剧不是在为杀人犯辩护。
而是用几乎令人窒息的情节,展示了胡冠骏成为凶手的全过程——
这个男孩,并非天生的恶人。
他自幼患有自闭、注意力障碍,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困难,交际能力差。
小时候无法专注画画、理解不了数学题。
因为难以管教,就被丢到外婆家。

长大后,又成为校园冲突的常客:
成绩差、行为异常、和老师顶嘴、与同学无法相处 …… 问题愈演愈烈。

父母本是中产阶级,经济无忧,也曾全力投入。
带他看病吃药、安排保姆、不停换学校。
但一次次复发、失控、校方和其他家长的投诉,让他们从「无条件的爱」逐渐滑向「沉甸甸的责任感」。
他们彻底放弃了,认定生了一个恶童,转而将重心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剧中有一幕,胡冠骏又和同学起了冲突,被老师叫了家长。
原本并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极力解释。
但因为他的「累累罪状」,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他。
父亲也第一时间怒骂,「为什么要搞这些麻烦?」


再后来被退学、被隔离,被送进医院。
精神科的医生很温柔,少年法官也对他充满耐心。
但在他眼中,那些善意背后,依然是一种区隔。
他感受到的不是「平等的照顾」,而是「被区别对待」的羞耻。

逐渐地,他学会了怎么表面上当一个正常人。
装出平静、有礼貌、懂规则的样子,好尽快离开医院。
但真正的连接没有建立,他始终是一个难以融入环境的异类。

成年后,他和父母渐渐断绝联系,靠打零工谋生。
也曾尝试「正常生活」。
交了女朋友,女友怀孕。
似乎命运开始松动。

可现实立刻反扑。
他在超市打工时,被同事排挤,被老板无故辞退。
他没有钱买药、缴房租,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
恰逢女友怀孕,他找到关心他的医师借钱,被拒绝。
找老板也无果,找父亲求助也被赶出门。

一气之下,才放火烧了老板的机车。
却没料,火势迅速蔓延,整个超市都被烧。
超市里的安全门因故障锁死,里面的人无法及时逃出,才酿成了人命。
受害者中,就包括那位始终关心他的少年法官和她年幼的孩子。


这场悲剧最残酷之处在于,胡冠骏并非被彻底放弃过。
他曾被无数人试图接住——但接住的人,不是系统,而是几个「个体」。
他们曾用尽力气托举他,却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不接纳。
而胡冠骏自己,也未曾没有努力过。

他的犯案,不只是他个人的崩塌,也是整个系统的失守。
在纵火案中丧生的少年法官及其女儿,恰是胡冠骏的精神科医生。
失去妻女后,医生也终于崩溃,甚至动了私刑复仇的念头。
这是人之常情。
可这种情绪,面对「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犯罪」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轻松作答。


能否避免一个精神病患成为杀人犯?
《与恶 2》没有轻易给出答案。
但它用「对照组」的方式,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剧中那位少年法官,之所以在所有人都放弃「问题儿童」时,执着地坚持陪伴,尝试感化。
是因为,她曾经也被认为是问题儿童,几乎要被父亲放弃。
但在她母亲不懈的陪伴下,不仅顺利长大,还成为一个相当优秀的少年法官。

还有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角色,同样因疾病导致家庭暴力。
在确诊后积极接受治疗,本已逐渐康复。
但在疫情期间,一次断药、加上社交隔离和恐慌情绪叠加,他病发并误杀了一名法警。
最终他被判无罪,但要监禁看护,接受进一步治疗。
经过治疗,他也变成了一个温和、负责的丈夫和父亲。


可能有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的确,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每次一有杀人犯因精神疾病脱罪的新闻,都有大量反对声。
因为这无疑挑战了有罪必罚的常识性认知。
人们会觉得失去了安全感,为受害者家庭觉得不公,呼吁死刑,或终身监禁。

但,和上一部所表达的一样,这部剧讲述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说明:
精神疾病不等于恶,防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才能真正预防、减少犯罪。
很多时候,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与恐惧,远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力。
每次患者失控,最先被指责的,往往是「为什么要让他在外面乱跑?」
可恰恰是这种标签、区隔、排斥、懒政 ……
让很多家庭不敢送孩子去看病,不敢公开寻求帮助。

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成为精神病医生,导致人力不足。
这一切,反而都埋下了更危险的因子。

剧中也精准地揭示了另一种悲剧循环:
当一个患病父亲入狱后,他们的孩子被推向社会边缘,到哪都受尽白眼,为求生存也走向犯罪道路。

这条悲剧的链条下,是恶的再生产,更是社会系统的整体溃败。
因而,当我们轻易地将「精神病杀人」归结为「个人问题」。
实际上是在对整个公卫系统、司法制度、社会支持网络的失职视而不见。

此外,很多人无法接受杀人犯因精神问题脱罪,也是因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
以为「因精神问题脱罪」就等于「免罚」,就是当庭释放了事。
其实远非如此。
他们往往要经历长期的矫治与监管程序,家庭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很多罪犯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制度本身就残缺不全,投入不足。

大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避免这些复杂、繁琐的工作,选择用私刑、牢狱之苦了结。
但这部剧最后,也发出追问:死刑真的能够救赎吗?
结尾,胡冠骏被判死刑。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可能是唯一能安慰受害者的方式。

但剧中角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到最后也没有求饶,没有因此痛苦。
甚至有人发现,他故意摆出冷血、玩世不恭的态度,似乎就像是在期待死刑。
对他而言,疾病所伴随的自毁性倾向一直没能根治。
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对他而言,就是解脱、是了结。
而这,恰恰让惩罚本身失去了意义。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与恶 2》在结尾留下一连串掷地有声的问题。
我们真有能力,让每一个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犯案前被接住吗?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法律与社会机制,避免「下一个胡冠骏」吗?
在死刑之外,我们是否能构建出真正的公共安全体系?
……
这都比判一个人死,更复杂,更难,也更重要。

这部写满了希望和绝望的剧,并不治愈,也没有提供答案。
但鱼叔认为它没有烂尾,是因为它确实完成了大部分华语剧都没能做到的事:
真正地直面恶的根源,并追问我们社会能否承受救赎的代价。
而在这个问题被回答之前。
我们与恶的距离,仍旧并不遥远。


全文完。
驰盈配资-炒股配资官网开户-股票配资开户手机版-配资平台炒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